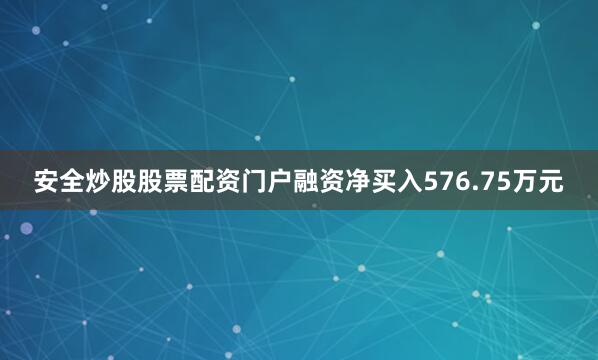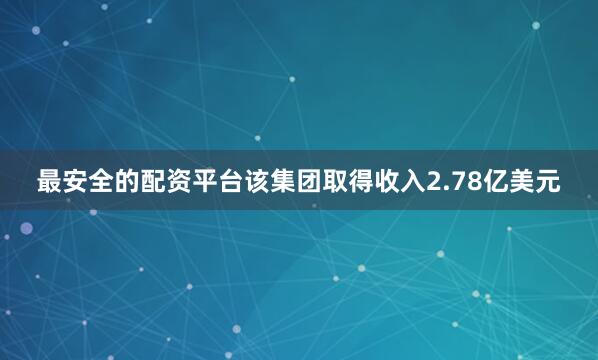(原标题:从债到股的博弈:私募股权基金可转债投资全攻略(下))
承接上文
从债到股的博弈:私募股权基金可转债投资全攻略(上)
四、可转债的典型投资场景:结构优势与阶段适配
“可转债”作为一种融合债权保障与股权期权的复合型工具,因其初期可控、后期可进、全程可退的灵活性,在私募股权基金实践中被广泛用于多类投融资场景。特别是在投资周期长、退出路径不确定的项目中,可转债不仅可作为阶段性资金配置工具,更能作为私募基金介入复杂项目的重要“缓冲机制”。
结合当前市场惯例及监管导向,可转债在以下几类典型场景中尤为常见:
·Pre-IPO 阶段提前介入
私募基金通过认购拟上市企业的可转债,在享有固定利息和兑付期权的同时,保留未来上市前以协议价格转为股权的权利。这种方式兼具“保底收益 + 资本增值”双重路径,常用于投前估值争议较大或挂牌进程尚不确定的项目。
·并购与重组融资
在企业并购、分拆或资产整合过程中,收购方或其控制股东因现金流受限,往往引入私募基金以可转债形式注资。该方式可实现对目标公司的阶段性介入,同时分担估值博弈与整合风险。转股机制也常与财务指标或并购完成进度挂钩,增强激励约束。
·产业协同与战略合作
对于具有协同潜力但暂不宜直接控股的产业类项目,私募基金可通过可转债结构设定阶段性入股机制,在“债性防守”下保持合作弹性,待战略成熟或时机合适再转为股权参与乃至控股地位。这种结构在医疗、教育、新能源等领域尤其常见。
·管理层激励与上下游绑定
可转债也常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工具或产业链绑定工具使用,通过设定分期转股、对赌条件、绩效达标等安排,实现对关键人群或合作方的“延迟授股”,增强利益捆绑与长期协作稳定性。
·监管提示:转股不能“虚设”
随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于2023年正式实施,监管层对“可转债”投资的结构合法性提出更高要求。条例第十二条明确指出:“附转股条款的债权投资,须与被投企业的经营指标挂钩,具有实现性。”
这意味着“转股条款”不得仅为结构合规而形式化存在,基金管理人必须能够证明转股路径的商业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若设置不具备实现条件的“空转股”机制,实际仍构成债性融资,可能被监管或司法认定为“变相借贷”或“名股实债”。
五、“转股条件”设定的合规边界与司法认定风险
正如前文所述,私募股权基金采用可转债结构,初衷在于兼顾风险控制与增值预期,特别是在投早期、估值不确定、信息不完全的项目时,通过设置“转股条件”实现阶段性过渡。然而,“转股条件”不仅是商业安排的技术性条款,更是判断该结构是否合法、是否构成“名股实债”的核心标准,在监管与司法实践中,具有高度敏感性。
1、转股条件的类型:因项目特征而异
在可转债合同中,基金管理人通常根据项目风险、行业特点、投资目的等因素,设置多样化的“转股触发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财务指标型
以被投企业达到特定营收、净利润或现金流指标为转股前提,如“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扣非后ROE不低于15%”等,体现对企业基本面改善的期待。
·交易指标型
将完成某些业务操作作为转股基础,如“完成收购上游原材料公司”、“实现海外渠道布局”等,适用于以并购整合为主的项目。
·合规/尽调型
针对企业初期存在历史瑕疵或信息不清的情况,设置第三方尽调通过或整改完成作为转股条件,常见于Pre-IPO或VIE重构类项目。
·融资指标型
以企业后续获得某一轮融资为转股触发,如“完成不少于1亿元的B轮融资,且估值不低于5亿元”,适用于项目动态价值评估场景。
2、法律风险提示:“转股条件”不得沦为“结构障眼法”
转股条件作为合同核心条款,必须具备商业合理性、操作可行性与投资目的真实性。若基金管理人通过人为设定难以实现或与企业发展无实际关联的条件,以实现“回避股权但获取收益”的安排,将可能构成“假股实债”,触及监管红线。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2021年1月),若基金投资安排本质为规避监管、变相从事债权融资活动,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甚至被吊销管理人资格。
3、提前还款风险防范:防“可转债”变“短期债”
实践中,尚未触发转股条件时,部分被投企业可能因资金充裕或战略变化,主动提出提前偿还私募基金的投资本金。这类情形虽表面上有利于基金退出,但也会引发结构定性争议。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不得提前还款”,则一旦被投企业主张提前清偿,法院极可能支持其主张,进而将整个可转债结构认定为借贷合同,而非具备转股目的的投资合同。
因此,投资协议中应当明确约定:在转股条件成就前,不得单方清偿本息或要求退出,或者设置合理的退出对价与条件限制,以增强“投资目的”的合同显性。
4、典型判例警示:“名股实债”将适用借贷规则
·霍尔果斯凯风资本诉苏州爱斯鹏公司案(2015苏园商初字第02772号)
该案中,原告作为私募投资机构与被告签署《可转债投资协议》,约定转股需满足一系列定制性条件,同时设置固定利息与回购安排。案发后,被投企业未满足转股条件,亦未支付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尽管协议形式为“债转股”,但其实质为“附条件债务合同”,因转股条件不具备实现性,回购安排已形成刚性兑付义务,最终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支持投资人主张本息回收。
·启示
法院重实体、轻形式,一旦可转债被认定为“非真实投资合同”,将适用《合同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私募基金在结构设计与争议解决中极为不利。
六、股东权利的结构穿越与转股路径中的权利安排
在可转债投资结构中,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安排天然具有“双阶段”特征:转股前为债权阶段,转股后为股权阶段。这一结构虽然在投资逻辑上连续,但在法律关系与权利属性上却存在本质差异。若在投资协议中未作妥善设计,极易引发私募基金“转股难”“权利弱”“治理失控”等实务风险。
1、双阶段结构解析:从债到股的权利演化
可转债投资通常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债权投资阶段
私募基金以债权人身份向被投企业出资,签署债务合同,设定利息、兑付期及各类附加义务。此时基金并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地位,原则上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等公司治理性权利。
第二阶段:转股实施阶段
在转股条件成就后,基金基于合同约定将债权转换为公司股权,成为《公司法》项下的“股东”,享有章程赋予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尽管上述两个阶段在法律属性上区分明确,但从基金的投资目的与监管备案角度看,整个交易仍被视为一次完整的“股权类投资”安排。
2、转股前的“准治理权”:债权工具如何渗透治理边界
尽管可转债阶段不具股东资格,但为保障投资安全,基金管理人可在合同中通过设定“准治理条款”,部分嵌入类股东权利,包括:
·财务披露义务:定期提供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税务信息;
·重大事项报告义务:如资产重组、债务担保、高管更换、重大诉讼等;
·限制性负面清单:约定不得未经基金同意进行特定行为(如举债、抵押、转让核心资产);
·提前偿还条款:设置提前清偿需经债权人同意,或需额外补偿。
上述安排虽未构成公司治理意义上的“表决权”,但从实质上保障了基金对项目运行的信息知情权与风险控制权,构成“类治理结构”的关键工具。
3、转股后的正式治理权:注意法律义务同步到位
一旦转股条件触发且执行完毕,基金将正式取得目标公司股权,成为《公司法》第四章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股份公司股东,享有:
·表决权(含章程修改、高管任免、大额交易审批等);
·分红权;
·优先认购权(《公司法》第34条);
·股权转让权;
·会计账簿查阅权;
·股东会召集权及其他特别权利(若协议中已约定优先股或特殊治理安排)。
此阶段,基金还需关注是否触发以下合规义务:
·是否构成对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或重大影响,从而触发《反垄断法》第21条经营者集中申报义务;
·是否需要履行公司章程修改程序、股东会决议补正等治理程序;
·是否涉及工商变更登记、税务申报与投资者穿透备案调整。
4、实务争议焦点:转股权的执行难题
尽管合同赋予基金“转股权”,但实践中常出现以下障碍:
·被投企业不配合工商变更登记,以拖延转股或拒绝承认股东身份;
·公司章程未预留转股条款或未约定“强制配合义务”,导致基金权益空转;
·原股东通过提前清偿或设立程序障碍否定基金转股权利。
司法角度提示
《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债权人享有实现合同利益的权利。”若企业违反协助转股义务,基金可主张违约赔偿。但能否直接由工商部门“强制协助登记”,仍存实操障碍。
综上所述,私募股权基金在可转债投资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债权与股权两阶段权利属性的差异与衔接,合理设计转股条件与权利安排,确保投资结构的合规性与实操性。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框架与风险防控机制支撑下,私募基金才能真正发挥可转债的灵活优势,实现稳健投资与权益保障的双重目标。未来,随着监管政策日趋严格,基金管理人应持续强化合规意识,严防“名股实债”等法律风险,推动可转债投资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的健康发展道路。
文 | 夏叶璐
编辑 | 麻艺璇
#投资干货#
名鼎配资-股票按天配资-炒股平台配资-可靠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